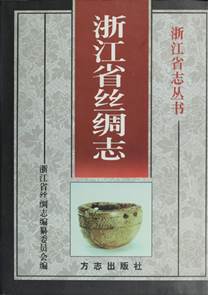
出版社:方志出版社
编纂单位:《浙江省丝绸志》编纂委员会
主编:《浙江省丝绸志》编纂委员会
概述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陆域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全省以丘陵山地为主,土壤肥沃,气温适宜,水网密布,宜于蚕桑生长。杭州、嘉兴、湖州、绍兴等均为浙江省茧、丝、绸重点生产基地。
素称“丝绸之府”的浙江,约6700年前人类已初步接触蚕丝,4700年前能完整地利用丝绸。历代帝王对丝绸生产倍加关注,并课以重税。随着人类进步和生产技艺提高,蚕丝绸天生丽质的特性被充分显露出来,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形成悠久灿烂的古丝绸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丝绸业走上了稳定发展轨道。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浙江丝绸业在弘扬传统技艺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产品档次,拓展国际市场,使浙江丝绸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浙江丝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闻名遐迩。
(一)
浙江丝绸生产的起源可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197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博物馆在宁绍平原的余姚县罗江公社东方红大队河姆渡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在第一期发掘时,于第四层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和动植物遗物中,有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纺织工具。这些出土文物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75年以同层同时出土的橡子用C14测定年代为距今6725±140年。1977年冬第二期发掘时,又出土了一个盅形雕器,上面刻着四条蚕纹。看起来象蚕在向前蜿蜒蠕动,头部和身上横节纹非常清晰。结合遗址第四层同时出土成堆的稻谷和木结构房屋,可知浙江先民已进入从事耕作的定居生活,标志着人们对蚕织的初步接触。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博物馆在吴兴县钱山漾两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探坑22号第4层,出土了丝线、丝绳、麻布、稻谷、细麻绳、棕丝刷子,以及盛有绸片、丝线、丝带、麻布片等物的竹筐。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735~2175年(距今4140~4700±85~100年)。通过观测鉴定,绸片是茧丝无捻合的长丝做经纬,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表面细致、光洁、丝缕平整。成为迄今中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丝绸实物,标志着浙江劳动人民早在4700年前已广泛地应用丝绸,其丝织技艺亦达较高水平。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浙江出产以彩色贝壳为纹样的“织贝”。《尚书·禹贡》记载了禹定全国为九州和各州出产进贡情况。其中规定上贡丝和丝织物有冀、兖、青、徐、扬、豫、荆等州。当时浙江属扬州之域,有出产进贡“厥篚织贝”记载。“织贝”是一种先染丝而后织成贝纹的锦名。
从西周(公元前10世纪末至前8世纪)起,麻和蚕丝已成为衣服的主要原料。西周官府设典妇功(专管丝麻生产)、典丝(专管蚕丝验收、贮藏和分配)、氏(掌练丝帛)和染人(掌染丝帛)等官职,并建有“公桑、蚕室”和“百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列国争霸,均奖励耕织。浙江当时为越国,居今浙东(南)和部分浙西(北)。另一部分浙西(北)地区则属吴国。从公元前497年吴国战胜越国到公元前473年越国灭掉吴国的二十多年中,勾践采纳谋臣范蠡和文种提出的“必先省赋敛,劝农桑”(《绝越书》卷4)等建议,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史记》卷41),丝绸生产得到提高和发展。春秋后期,越国生产的丝织物中有币、帛、采、罗、纱等(《嘉泰会稽志》)。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战国七雄争霸局面,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后,沿袭商鞅之法,鼓励耕织,丝绸生产继续发展。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军需浩繁,对谷帛之需,尤为迫切。故奖励力田,提倡食货并重,并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以农桑为本。汉时浙江会稽一带的蚕织生产已有相当水平。《后汉书·朱传》记载:会稽人“朱少孤,母以贩缯彩为业,同郡周规,负官债百万,县催责之,窃母帛为规解债”。这反映会稽(今绍兴)一带,不仅蚕织较盛,且有贩卖巨额缯帛的商人。1958年杭州古荡发掘出一座汉墓,死者朱乐昌夫妇尸体上,盖有丝麻织物的被子。看来除浙东(南)会稽等地外,浙西(北)一带,也多蚕织。三国鼎立时代(公元220至280年),浙江属吴国。吴国的官营织造,扩展很快。“后宫列女诸织络及徒坐”的人数,由孙权时的“数不满百”增至孙皓时的“千数”(《吴志·陆凯传》)。三吴地区许多大族地主,也经营丝绸生产。农民是当时丝绸主要生产者。他们把蚕织作为重要本业,上纳贡赋,下维生计。吴国统治者消费(包括馈赠等)丝绸数量很大,亦常资取于西蜀。吴国丝织业,尽管以浙江为主的三吴地区有了较大发展,但整个说来,还至魏、蜀之下。
两晋、南朝时期,赋税极重。当时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会稽)已被统治者视为“随土”作赋而征收丝帛地区,农民必须用丝帛交纳数量日增的赋税,因而不得不竭力蚕织。浙江的丝绸生产,从西晋(公元265至316年)起,就是在重课之下发展的。永嘉等地,为了增产蚕茧,已重视一年“八辈蚕”的饲育(《永嘉郡记》),并贡八蚕之绵(左思《吴都赋》)。又据《两浙名货录》载,建德在“男丁种桑五十株,女丁半之”的劝课下,“顷之成林”。《刘户曹集·东阳金华山栖志》载,东阳、金华、新安等山区盛植桑树。吴郡、吴兴郡等平原地区,普遍植桑,已“荫陌复垂塘”(《吴朝清集》)。又据《吴兴记》载:乌程县东南三十里,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成丘桑林。随着丝绸业的发展,蚕织技术也不断提高。据《晋书》卷124《慕容宝传》载:“先是辽川无桑,及(慕容)宝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当时吴郡统吴兴、嘉兴、海盐、盐官、钱塘、富阳、桐庐、建德、寿昌等县。可见早在1600多年前,浙江的部分地区,已有优良桑品种育成,故远道南来而求之。南北朝时期(公元420至589年)会稽(今绍兴)已是米、绢等物交易中心,《宋书》记载:朱伯年“有时出山阴,为妻买缯彩三五尺”。这是当时民间丝绸交易和服用的典型例证。到梁时(公元502至557年),浙江民间织女能织成镶金薄(线)的罗(沈约《沈隐候集》卷4)。丝织品织纹和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妙,不可名状”(《吴越钱氏志》卷23《志余》)。当时浙江丝织技艺水平可见一斑。
隋代(公元581至618年)浙江农民继续扩大蚕织生产,永嘉、新安(淳安)、遂安等地普遍推广“一年蚕四、五熟”的增产经验。同时,会稽等地不少官僚地主和寺院地主,也扩大了蚕织经营,丝织技术提高很快。如越州进贡的耀光绫,“绫纹突起,时有光彩”(颜师古·《隋遗录》卷2)。
唐代前期,中国蚕织生产区域仍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丝绸在产量和质量上均不及北方。安史之乱后,丝绸生产重心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南移。江南道在全国丝绸生产和贡赋方面占据重要地位,而浙江尤为突出。《吕和叔文集》载,唐王朝已“辇越而衣”。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关于贡赋的记载,全国有一百多个州郡上贡丝物,江南道占其中的五分之一。在江南东道的十九州(江苏四州、浙江十州、福建五州)中,上贡丝、绵及丝织品的共十三州,浙江在湖州(吴兴郡)、杭州(余杭郡)、睦州(新安郡)、越州(会稽郡)、婺州(东阳郡)、衢州(信安郡)、处州(缙云郡)、温州(永嘉郡)、明州(余姚郡)共九个州上贡。
唐代,浙江的丝绸生产水平以会稽郡越州最高,发展最快。《会稽掇英总集》卷9载:越州“产业论蚕蚁”,蚕织生产已成为很重要的社会生产。据《旧唐书》载,天宝二年(743年),唐玄宗登望春楼,观看各郡装载特产的漕船在广运潭中缓慢前进的盛况,其中会稽郡的船载有铜器、罗、吴绫和绛纱。又据《元和郡县志》载,越州在开元时,贡品只有交梭白绫一种。到了唐后期,《新唐书》记载,贞元时,除纳规定贡物之外,还进贡异文吴绫及花鼓歇纱、吴绫、吴朱纱等数十品。尤其是每年所进贡的缭绫,其织纹之精妙,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敬宗即位(825年)后,曾下诏索取“盘绦绫千匹”(《新唐书》卷180)。说明越州在唐代,蚕织生产发展迅速,已成为江南新兴的丝织业中心。浙江的“丝绸之府”地位初具雏形。浙西地区的丝织业在唐代后期发展亦颇为迅速。如吴兴郡进贡的除绸、绵外,还有名贵的御服乌眼绫以及纤缟等。再如钱塘郭外东北均为蚕桑地,而且在开元以后,不但生产绯绫、白编绫、纹绫等贡品,还生产柿蒂花纹的绫,十分精美。唐朝末年,中国出现五代(公元907至960年)十国(公元902至979年)混战的局面,浙江属吴越国。吴越王钱镠自知吴越是小国、弱国,采取不谋争夺,但求偏安,积极推行“闭关而修蚕织”(袁枚《重修钱武肃王庙记》)政策,在农村和城镇,甚至寺院推行栽桑养蚕织绸。钱镠在杭州西府设立丝绸手工作坊,大量生产绫、锦、缎等高档丝织品,开创了杭州官营织造先河。吴越国使吴越时期的蚕织生产发展,正如钱文选在《追述钱武肃王治吴越功德纠正欧史非议之谬诬》一文中所说的,“遂劝民从事农桑,桑麻蔽野。至今千余年,江浙丝绸业,为全国之冠”。在北方连年战乱,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同时,在南方,特别是浙江的丝绸生产继续发展。
唐代,浙江丝绸商业十分兴旺,浙产丝绸在国内,经运河等通道大量运往京师,并畅销南北各地。外销方面,除经广州、泉州等处转运出口外,直接由杭州和明州(宁波)运往日本等国,为数亦巨。从杭州等地输出的丝织品,深受日本等国人民欢迎。唐代浙江逐渐成为王朝征收粮帛等赋税的重要地区,越州的缭绫和杭州的柿蒂绫征收与日俱增。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丝绸业技艺提高,品种繁多,倍受称道。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脍炙人口的《缭绫》一诗即是真实写照。
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南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北方,北宋(960年至1126年)统治者认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卷337)。北宋末年,中国丝绸生产重心向东南转移。在北方,由于辽、夏、金相继侵扰、劫掠和破坏,蚕桑丝绸生产出现停废、萎缩现象。而东南地区,特别是吴越一带,相对偏安,成为封建朝廷财政和包括丝绸物资重要供给地。宋初,为开发东南地区,曾一度实行了某些奖励垦殖措施,对浙江蚕织生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当时浙江有些地区蚕织生产之盛,正如《富国策》所描绘的那样:“茧薄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进行商品生产的“织帛之家”也不少。浙江除民间织造绢帛外,还有官办织绫务,有湖州织绫务和杭州织绫务两处。从北宋乾德五年(967年)至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的200多年间,两浙路(今浙江和江苏的江南部分地区)上供丝物占全国各路上供丝物总额的1/3以上,上供的丝绵则超过全国的2/3。北宋时,浙江丝绸交易十分兴旺,朝廷对丝绸贸易严加管制。如天圣元年(1023年),富阳县民蒋泽等提到商人沈赞,贩卖罗182匹,沿途偷税,因而完全没收入官。对海上贸易,宋王朝予以重视和奖励。如太宗雍熙年间(984至987年)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管理外贸的市舶司,除广州外,杭州、明州(宁波)亦有设置。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丝绸国内外销路的扩大,刺激了浙江丝绸生产发展。
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亡而皇室南迁临安(杭州),建立南宋(1127至1279年)。南宋王朝偏安江南,极力扩展丝绸生产,对重点产区浙江倍加重视。从事蚕织业的主要是农民,但也有少数官商巨室。随着商品性丝绸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缫丝和织绸分业现象。当时,城市的丝织生产已相当发达,如杭州,除武林门外夹城巷晏公庙的官办织锦院有织机三百余张外,私营丝织作坊也不少,有些作坊还雇工生产。杭州的许多彩帛铺,除经商外,几乎都兼营织染手工业。在婺州也有彩帛铺,并设有作坊,兼营织染等业。绍兴蚕织业此时更有发展,所谓“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和“万草千华,机柚中出,绫纱缯縠,雪积缣匹”(《会稽掇英总集》卷20),正是该地区丝织业发达情况的概括。嘉湖地区的蚕织生产发展迅速,除原有生产的城镇外,有些原来是很荒凉的乡村,也发展成蚕织城镇,如濮院、崇德、安吉等地机杼声不绝。
南宋朝廷重视丝绸生产科技水平提高。四明(宁波)人楼璹,在高宗绍兴年间(1131至1162年)任於潜令时,“笃意民事,概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至剪帛,凡二十四事”(楼钥《玫瑰集》卷76)。浙东提举朱熹还印发王文林的《种桑法》,以“榜谕民间”。宋代织造术很高,浙江丝织品种多,花样精巧。据《梦梁录》和《咸淳临安志》记载,杭州的绫有白编绫、柿蒂绫、狗蹄绫等品种;罗有素、花、缬、线柱、暗花、金蝉、博生等;锦有青红捻金锦、绒背锦;缎有销金线缎,还有混织杂色线的花缎,即所谓“锦裥缎子”等等。吴兴的樗蒲绫、安吉的丝、绢、纱,武康的丝绵、双林的纱绢、崇德的狭幅绢、濮院的濮绸、台州的绫、婺州的罗等制作精美无比。绍兴地区的越罗更是驰名中外。诗人杜甫曾有“越罗蜀锦金粟尺”的诗句。
南宋杭州是商业最繁荣的大城市,经营丝绸的名家店铺很多,如市西坊南家、吕家、陈家的彩帛铺,市西坊北钮家的彩帛铺,清河坊的顾家彩帛铺等。绍兴、湖州等地生丝绵帛铺也很多,且买卖昼夜不绝。对外贸易方面,南宋朝廷认为“市船之利最厚”(《宋会要稿》“职官志”44),而加以重视。大量丝织品从宁波港输往日本、朝鲜、阿拉伯等国。除大量的锦、绫、缬、绢等丝织品外,并有蚕丝出口。
元朝(1271至1368年),浙江丝绸生产进入了艰难经营时期。元朝统治者的军队、蒙古贵族和僧侣等,侵占大量民田,仅浙西所谓公田,即达75万顷。贫民由于租赋繁重、徭役苛逼,生活凄惨。有些甚至被典卖为“驱丁”(近乎农奴)。严重地阻碍包括蚕织在内浙江农业和手工业的继续发展。此外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需要,俘虏和征括工匠,动辄从数十万计,大批江南丝织巧匠被俘征和掠卖,大大阻滞了浙江民间丝织手工业的提高和发展。
后来元朝统治者,逐步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杀掠方法,重视农业生产。为能获得更多丝帛,对蚕桑生产加以重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行《农桑辑要》,广传生产知识。到元中期,浙江蚕织生产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稍有提高。许多农民尽管处境较恶,但为了缴纳丝税和维持生计,仍在坚持蚕织。由于大办官营织造,所需原料大增,租赋大都由绢变为“丝料”,故入元以后缫织分业更有发展,这有助于缫织两业生产质量的提高。湖州地区对种桑养蚕缫丝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经验。随着缫织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独立经营的手工业作坊(织户)日益增多。元中叶浙江各地的丝织业,多数已恢复到宋时水平,如金华、濮院和双林以及崇德等地都增添了丝织新品种。元朝官办丝织业较多,除专设“纳石失”(织金锦)局外,还有绫锦局、织染局、罗局、绣局等等。在杭州等地设有文锦局和织染局。官营织造的原料除夏税之外,还向民间收买一部分。对上供的绸缎必须用高级细丝、上等染料,由手艺精湛的工匠染织。元代重视对外贸易,先后设置市舶司七处,浙江有庆元(宁波)、澉浦、温州和杭州。主要出口金银铜铁、丝与缎匹。海商远溯钱塘江而上,向建德等地收购生丝。元代湖丝初露头角,名声渐振。
明代(1368至1644年)社会经济全面进步,丝绸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促进了浙江丝绸生产技术提高和丝绸商品经济显著发展,浙江丝绸举足轻重,“丝绸之府”地位进一步巩固。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所记载的大部分是反映当时浙江的情况。栽桑方面,除利用嫁接法外,压条法也广泛使用。养蚕方面,对蚕种选留、保护以及新品种培养十分讲究。为提高蚕茧解舒率,总结出“出口干”三字诀。缫丝方面,广泛采用两人操作的足踏缫丝车。生产“合罗”(细丝)、“肥丝”(粗丝)。制丝用水选择注重一个“清”字。丝织方面,明代织机有三种类型:腰机、小机、花机。《天工开物》载: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明代浙江花机更加精简完善,结构科学,推动了提花织物更大发展。只要由画师作出小样、就能在织物上织成花纹。浙江是当时高级锦缎和龙袍重要产地,此与丝织技术水平提高密切相关。由于织造练染技术进步,浙江丝织物品种繁多,花色鲜艳,民间丝织品种,据明成化《杭州府志》载,有缎、罗、锦、剪绒、绫、绸、纱、绢等。双林倪姓独家所织奏本用绫上有二龙,龙睛突起有光亮,列为极品。湖丝、吴绫、皓纱、温州缂丝及浦江女诗人倪仁吉的刺绣艺术均为明代浙江丝绸名产,久享盛名。
明代浙江丝绸生产的特征是商品生产。明代赋税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等实物,因此不生产丝绸的省份,须向产地采购以上贡。统治者向西北及东北少数民族换马等贸易所需高级丝织品也以浙江生产为主。因此,浙江丝绸在国内行销极广。明代中叶以后,除杭州等大城市丝绸交易频繁外,还出现了许多丝绸工商市镇。如菱湖、南浔、双林、濮院、王江泾、石门、塘栖等。南浔所产七里丝(辑里丝)质量最佳、闻名天下。杭州、嘉兴、湖州成为浙江丝绸重点产区。
丝绸一直是明朝重要输出物资之一。浙江当时已成为全国丝绸基地,输出的丝织物,以浙产为多。丝绸输出,尤其是生丝,可以获得原本两倍或数倍利润,如傅元初在《请开洋禁疏》中说“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两倍”。因此,明朝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丝绸被列为禁品之一。《万历会典》载有规定:“凡将缎匹、、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载之人减一等,货物船只并入官”。但浙闽许多商人仍常犯朝廷海禁之令,私贩丝绸货物出海,官府经常查获私商通倭案件。明代严禁私人与外国互市,设市舶司于广州、泉州、宁波等地控制海外贸易。十七世纪中国海上贸易主要港口,逐渐由福建向浙江转移。
清代前期(1644至1840年),浙江种桑、养蚕、缫丝等生产技术,在前代基础上逐步提高。桑叶亩产春叶,好时2500多斤。养蚕技术方面总结出“十体”和“二戒”的经验。缫丝对原料选剔有所改进,对缫丝水质十分重视。尤以七里湖丝,质量为全国之冠,康熙时温棐忱《七里村志》记载有“七里丝名甲天下”,并畅销国内外。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设有官营织造局,主要提供“上用”和“赏赐”缎匹,满足宫廷和官府所需。清代民间丝织手工业发展较快,杭州、双林、濮院、塘栖等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杭州、绍兴等地有先织后染的“生货”如罗、纺、线春、绫、绢类,有先原料丝练染后织造的“熟货”,如宁绸、缎子、线绉、纱、蟒袍等类。与丝织业相适应的行业也相应发展,如练染业,绍兴一带相当发达。因此,浙江在清代丝织品名目繁多,精彩夺目。如花纺绸、素绢、画绢、锦绫、花罗、湖绉、杭绸、包头绉等,杭州民间织造的西湖十景图更是维妙维肖。
清代前期浙江丝绸除供本省消费外,以远销京城和东北最多,广东、福建、江苏次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业绸者出资在杭州忠清巷建屋设置“绸业会馆”(即“观成堂”),为业绸者议事之所。外贸方面,浙江所产生丝、绸缎,尤其是湖丝,为外商所竞购。主要销往日本、英国等国,除丝货输出外,浙江的染料也大量出口,为国家换取大量白银和墨洋。
(二)
清代后期(184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8年)的100多年间,浙江蚕丝业饱受蹂躏,在困境中生存。机械缫丝业兴起、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掠夺、蚕丝教育改良和蚕丝统制管理成为浙江丝绸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蚕学馆,这是浙江兴办蚕丝教育的开始,也是中国最早的蚕丝教育机构。
法国于1828年发明利用蒸汽为动力的缫丝机,英、法、日等国缫丝、丝织业相继采用机械化生产。浙江缫丝业还停留在手工缫制阶段,所生产土丝质量逊于厂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浙江省相继兴办开永源、世经、合义和、大纶、公益5家以直缫式缫丝车为主要设备的机械缫丝厂,标志着浙江缫丝业进入了机械缫丝阶段。同时,浙江缫丝业走上了改良土丝的道路。南浔等地在土丝价格和销路不如厂丝的情况下,曾用“摇经”办法,把辑里丝摇成“干经”。将旧式缫丝车加以改良,把分散于农家土丝车集中以工场形式缫丝。
鸦片战争前,浙江丝织手工业分工精细,有专业络经作坊,牵经铺、挑花匠、捻坊、料房、绒经染坊等,整个丝织手工业经营,多为商业资本控制,组织形式主要有绸庄兼营机坊、独立自营、放料代织、丝织工厂4种。产品质量、花色均有提高和创新,品种达300种左右。如杭绍的宁绸、缎、线春、罗、纱;嘉湖的绉、纱、绵绸等。
自19世纪20年代起,法、意、英等国对丝绸机械的广泛应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对蚕茧和生丝需求与日俱增。外商在上海开设茧行、丝行、开办丝厂,大量压价收购浙江蚕茧、生丝。丝行是外国资本掠夺生丝的主要渠道。五口通商后,浙江各产丝地区开设许多丝行,如长兴一带不下百余家,余杭有5家,杭州有76家。大部分浙江生丝转手外销或外商直接收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洋商、沪商纷至浙江设茧行或租行买茧。
资本主义列强不仅掠夺蚕茧生丝,而且扼杀中国丝绸业,倾销自己的丝织品,采用“引丝扼绸”政策。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把洋绸等产品进口税率和我国蚕丝出口税率大幅降低,如将湖丝出口税率由9.43%降为3.97%。资本主义国家还利用从中国掠取廉价蚕茧生丝制成洋绸,再向中国倾销,阻挠中国丝织物出口。因此,浙江丝织物外销锐减,内销不振。如嘉兴地区销出丝织品,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为2775担,而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则减至228担。杭州销出丝织品,光绪二十五年4193担,光绪二十九年减到1784担,到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绸缎受洋货影响,著名的湖绉、濮绸等销路日减。内销方面,经销丝织品的纱缎庄、绸缎庄和锦缎庄,受进口洋绸和时局不稳及苛捐杂税影响,丝织品内销时增时减,到宣统三年(1911年)大幅下降,浙江丝织业呈现停滞和衰落景象。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十分重视蚕丝生产,并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按4.5亿人每人用绸缎2.5米,即需蚕茧850万公担,生丝7.1万吨,产绸缎11.25亿米”的远大设想。民国3年(1914年)正值帝国主义爆发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辛亥革命后,政府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一系列改良蚕丝业的措施。主要是设立蚕丝教育和实验机械,进行技术推广指导,制订蚕丝统制的有关条例法规。如筹办模范丝厂(1913年),采用新法缫丝;成立浙江蚕桑改良会(1919年);制订茧行条例和丝厂条例(1919年);将统制收茧缫丝纳入省建设厅蚕丝统制委员会领导(1934年)等。对浙江蚕丝业生产发展起推动作用。浙江在这一时期,除蚕桑生产保持上升外,缫丝和丝织生产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过渡,绸缎花色品种有较大更新,蚕丝科教有一定发展。除原有合义和、大纶、公益3家机械缫丝厂继续兴办外,新的丝、绸厂不断出现。民国元年(1912年),朱光焘(谋先)邀集杭州官绅、富商集资在杭州池塘巷成立纬成公司,成为当时浙江最大规模的民族资本丝绸工业企业。民国3年(1914年)杭州虎林公司成立,设花机10余台,专业织造三闪缎、实地纱等。同年,杭州创办武林铁工厂,试制引擎、坐式缫丝车等。民国6年(1917年)制造丝织机和提花机,仿制东洋纡车等,扭转了浙江丝绸机械依赖进口的局面。民国4年(1915年)天章绸厂成立。纬成、虎林、天章相继在厂内设缫丝部。民国18年(1929年)浙江省建设厅拨款在杭州武林门外兴建杭州缫丝厂,引进了群马式立缫车等设备。同年至民国22年世界经济危机,浙江民族资本所经营的近代丝绸企业陷入困境。民国24年秋季后,国际丝绸市场好转,浙江丝绸业得以扩充。同年,全省有大小缫丝厂(包括绸厂缫丝部)29家,缫丝机7598台,民国25年浙江厂丝生产量609.69吨。这一期间,由于蚕丝改良和引进、仿制日本先进丝绸设备,尤其是引进日本提花织机等,使浙江的“蚕猫”牌生丝、“孔庙”牌绢丝、七里湖丝等名牌产品饮誉海外。杭、嘉、湖、绍生产的绸缎花色品种更是丰富多彩。浙江的绸庄一度发展很快,著名的有悦昌文、蒋广昌、袁震和等。民国23年,已有20年历史,在白莲花寺前(今新华路)设立的丝绸交易茶会改组为“杭州市绸业市场”,成为机户、绸庄的重要交易场所。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浙江时,沪杭铁路线两边桑树全部砍伐,沦陷区的丝厂、蚕种场、蚕丝教育科研机构惨遭洗劫。民国27年,侵略者在日本蚕丝国策会社名义下,纠集日本蚕丝垄断企业218个单位共同投资,在上海成立华中蚕丝公司。在浙江成立杭州、嘉兴分公司,在湖州、长安、硖石、海盐设办事处。华中蚕丝公司成立后,颁发了《管理丝茧事业临时办法》、《关于蚕丝事业统制指导要领》等一系列法令,规定蚕种、茧丝绸、销售等统由华中蚕丝公司经营控制,从组织上建立了一套掠夺浙江蚕丝的体制。据不完全统计,民国27至32年杭州纬成、庆成、天章、长安等厂所生产的2万担生丝全被掠夺。抗日战争期间,浙江丝绸产区遭受严重摧残。国民党统治的浙东地区虽有丝绸厂及蚕丝行政机构,但仍朝不保夕,惨淡经营,民国25年至民国35年底相比,浙江省桑园面积由365万亩下降至99.5万亩,产茧量由46800吨下降至8850吨,丝车由8526台下降至3776台,产绸量由300万匹下降至50万匹。素称“丝绸之府”的浙江蚕丝业元气大伤,一落千丈。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蚕区农民渴望恢复蚕业生产,民族资本工商业者和科研教育人员也极力想恢复发展丝绸业。但在国家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下,实行垄断压价收茧,苛捐杂税,致使蚕农无力扩大生产,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丝绸业发展。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致使民族资本经营的丝绸厂亏损增加,到民国37年(1948)缫丝厂仅存11家,绸厂、机坊中机台有四分之三被关停,丝绸产量大幅滑坡。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对浙江省蚕桑丝绸业恢复和发展十分重视。先后派驻军代表接管中国蚕丝公司杭州办事处、五丰绸厂、崇裕丝业公司、嘉兴绢纺厂、长安丝厂、嵊县锦源丝厂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人民政府以加工形式委托丝厂代缫生丝,当年全省有11家丝厂陆续开工,私营绸厂60%的织机为国家加工绸缎,奄奄一息的丝绸生产逐步复苏。1951年1月,浙江省工业厅召开首次缫丝工业会议,提出“巩固和扩大原有收购基础,鼓励私人资本投入生产,用以丝易茧为主的办法,恢复浙江缫丝工业”的方针。1952年杭州开源丝厂试验烘茧煤灶成功,烘茧效率比老式柴灶提高30%,燃料费节省50%,并迅速推广。同年还推广了立缫操作法,陆续全部改坐缫为立缫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至1957年),浙江省丝绸行业进入全面的公私合营,完成了对丝绸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7家缫丝厂经过停、转、并,调整为16家,并于1956年转为地方国营5家,公私合营11家。579家丝织企业调整为108家,其中地方国营3家、公私合营29家、小型私营76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第一家规模最大的丝绸企业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经国家批准于1956年正式动工兴建,引进日本多摩—10型自动缫丝机等先进设备,于1958年5月开始,丝、绸、印染各车间先后投入生产。“一五”期间对丝绸生产质量提高十分重视,各厂经常开展操作训练,互相观摩、评比,总结先进经验,并加以推广。1957年召开全省第一次绸缎花色品种设计会议,对历史上的丝绸品种,进行了有计划的挖掘与整理,推陈出新,创造了许多优良的新品种,扩大了销路。杭州胜利试样厂等单位为建国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设计、试制了一批高级装饰用绸。这一时期对发展浙江省蚕桑丝绸事业都有重要的影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1957年),桑蚕茧收购量由1949年的4500吨提高到19270吨;桑蚕丝产量由1949年的339吨增加到2099吨;绢丝由1949年的94吨增加到241吨;丝织品由1949年的1212万米增加到3181万米。整个丝绸业稳步健康地发展。
1958年以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失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影响,蚕桑丝绸生产一度大幅度下降。1962年全省丝绸工业总产值28265.9万元,生产桑蚕丝964吨,绢纺丝308吨,丝织品5952万米。1963年后,全省丝绸行业认真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三统一优”的原则(统一计划、统一原料、统一检验和择优安排生产),确定全省缫丝工业保持常年生产6家(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浙丝一厂、嵊县丝厂、顺丰丝厂、菱湖丝厂、坎山丝厂),停止生产5家,实行季节生产8家,全省缫丝工业精减职工6723人。由于认真贯彻八字方针,企业管理有了加强,产品质量逐步提高,蚕茧生产回升,人丝货源增加,丝绸外贸出口供不应求。为适应对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多创外汇,国家发放专用贷款,新增与扩大印花、缫丝、织绸生产能力,对老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全省丝绸工业形势全面好转。1965年底,全省共有丝绸企业64家,其中国营企业50家(丝厂18家、绸厂26家、印染厂3家、化纤厂1家、绢纺厂1家、纺机厂1家)。丝绸工业总产值3.77亿元,占全国丝绸工业25.76%,桑蚕丝产量1832吨,占全国35.23%,丝织品产量8153万米,占全国23.8%,均居全国首位。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从1957年起,浙江白厂丝直接向苏联出口交货,1964年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白厂丝1571吨,各种绸缎也通过上海或对苏直接交货而大量出口。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浙江丝绸业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许多传统丝绸产品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等一大批大中型丝绸企业停工停产,使全省丝绸工业总产值10年中只增长9%,1976年人均创利仅25.02元,相当于1965年1212.12元的1/48。但由于10年中广大丝绸职工和科研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在科研、生产方面仍取得一定进展。如新的蚕品种育成和推广,蚕茧干燥理论的探索和设备改进,新型自动缫丝机和丝织机自动化研究试制等。1972年全省蚕茧收购彻底改变手估目测的评茧计价办法,全面推行干壳量评茧计价。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稳定,改革开放政策得到贯彻。蚕茧生产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调动了蚕农积极性,促进了蚕茧原料增产增收。1978年全省桑园面积127.3万亩,产茧46830吨。丝绸工业认真贯彻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政府对丝绸工业在原材料、贷款、技改、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等方面给予优惠,浙江丝绸出现了欣欣向荣局面。嵊县丝厂缫制出6A级白厂丝,浙江制丝一厂生产出口一批11/13旦3A级高品位丝。凤凰牌62035交织织锦缎等丝绸产品被命名为部级名牌产品。在全省科技大会上,浙江省丝绸行业的提花丝织物纹制工艺自动化等9个科研项目获得一、二、三等奖。这一期间,浙江丝绸行业开始着手全行业技术改造,都锦生、天成、达昌、幸福等一大批老丝织企业和一些“弄堂棚儿厂”通过改建扩建,面貌焕然一新。制丝、绢纺、丝织和印染等行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引进自动缫丝机、精纺机、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等先进设备,丝绸行业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
(四)
1981年,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浙江丝绸自开口岸、自营出口。从此,浙江丝绸进入了大步跨入国际市场的崭新时期。当年,省公司就与世界上41个国家和地区455家客商建立了贸易关系,全年出口创汇1.08亿美元。为适应浙江丝绸内外贸所需,“六五”期间(1981年至1985年)投入1.14亿元对50多家缫丝、丝织、印染、绢纺、针织、服装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研制和引进先进的印染等后整理设备。为改变过去浙江丝绸丝类产品和坯绸面料居多的局面,于1981年利用省丝绸公司与地方联营,经过厂房、技术改造,兴办13家丝绸服装厂。浙江省在深圳特区的第一家丝绸中外合资企业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85年10月正式投产。同时省公司与有关厂家合作,开发真丝针织、和服腰带、缂丝、丝织地毯、丝绸时装等新产品,使浙江丝绸业在“六五”期间得到长足发展。1985年全省桑园面积131.17万亩,产茧84575吨,丝绸工业总产值17.43亿元,丝类产量11226吨,绸缎类产量33895万米,服装产量373万件,出口创汇2.055亿美元。
1985年1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浙政[1985]14号文《关于全省丝绸行业经济体制改革试行方案的通知》。决定成立浙江省丝绸联合公司,又称中国丝绸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领导管理,在外贸业务上受中国丝绸公司领导,外贸行政和管理上受省经贸厅领导。联合公司由省轻工业厅丝绸公司和省商业厅百货公司、省供销社特产公司中管理蚕茧、丝绸的机构和人员组成,实行经理负责制。文件规定,省属丝绸生产企业全部下放,从1985年春茧开始,蚕茧经营管理体制下放,丝绸生产和收购实行指导性计划。克服了多头领导、分散管理的弊端,调动了地方积极性,确保了蚕茧、丝绸、外贸专业协作及协调发展。1986年,浙江省丝绸行业加快了技术改造步伐,落实资金1.05亿元,用汇299万美元,进行骨干丝绸企业厂房、设备改造,并引进片梭、喷水、剑杆织机等先进设备,增强了发展后劲。年初,白厂丝大量积压,为消化白厂丝,省公司通过落实经济扶持等办法,努力扩大真丝绸生产出口。同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组织21家丝绸服装企业生产出口丝绸服装,全年出口丝绸服装210万件。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14号文件精神,积极倡导丝厂“一条龙”收茧,全省经批准12家丝厂(52个茧站)直接收烘茧,为减少环节、提高茧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7年,全省丝绸企业根据国务院、国家经委、省政府有关精神,深化改革,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不同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丝绸系统内成立了9个省级先进企业标准起草小组,开展企业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工作,22家丝绸企业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先进企业,同年还成立了浙江省丝绸企业管理协会。为提高丝绸产品档次,杭州福华丝绸厂、湖州南浔丝厂、嘉兴丝厂等进行厂房扩建和引进先进技术。全省缫丝、丝织行业组织出口产品厂际质量竞赛,开发丝绸高新产品,当年开发投产新品种、新产品1000余只,获部优产品8只。这一年,全省丝绸行业经济效益有较大提高,全年全省丝绸工业实现利税3.3亿元。
1987至1990年,是浙江丝绸史上极不平凡的一个阶段。第一,世界经济的普遍景气,国际上对天然纤维的爱好,丝绸砂洗工艺的应用,国际丝绸市场出现了旺销局面。中国白厂丝出口价格1986年为2.7万美元/吨,1987年为3.3万美元/吨,1989年达到5.0万美元/吨。第二,浙江省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小丝厂、小绸厂如雨后春笋,造成蚕茧、厂丝原料供不应求,从而引发了“蚕茧收购大战”。1987年春茧收烘期间,海宁、桐乡、德清、余杭和江苏吴江等县市及毗邻地区发生大幅哄抬收购茧价的蚕茧收购大战,随后愈演愈烈,波及苏、浙、川、皖、豫、鄂等省。尽管有关部门调动人力物力,制订政策措施,但随后更剧烈的中秋茧收购大战扑面而来。为此,1988年6月6日,即春茧收购前夕,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蚕茧管理防止抬价抢购的通知》,同年9月22日又发出《国务院关于茧丝绸收购和出口全部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的紧急通知》。浙江省是“蚕茧大战”主要地区之一,省政府成立省蚕茧收烘领导小组,由省工商、物价、财政、供销、经贸和检察等厅局长带队,赴全省各收茧地区,组织各市县力量维护蚕茧收烘秩序,稳定收购价格,对茧农政策引导,对茧贩围追堵截。直至1990年,由于国务院、省政府高度重视,加上国际丝绸市场“丝绸热”趋于降温,历时4年的“蚕茧收购大战”才得以基本制止,但造成茧质下降,生丝生产能力过剩等负面影响。第三,国家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严峻冲击。这一期间,茧、丝、绸生产收购仍由国家主管部门下达计划,尤其是蚕茧、生丝、坯绸属国家一、二类出口产品,严格按出口许可证管理。在省内,茧丝绸生产经营分属农、工、贸多头管理,省市县财政分灶,各部门因利益所驱,关系难以协调,致使在蚕茧收购、工业生产、出口等方面矛盾重重。地方利益促使丝绸加工能力盲目扩大。在国际市场上,非正常渠道出口的生丝、绸缎(时称“水货”)占据很大比例,出现对内抬价抢购,对外降价竞销的局面,使浙江丝绸遭受很大损失。第四,1988年国务院为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步伐,确定了“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实行代理制”的工作方针。浙江省丝绸行业多年来丝绸由省公司统一收购出口的专营丝绸出口体系开始打破,为期3年的浙江丝绸第一轮外贸承包开始实行。当年,将出口收汇、上交外汇额度、出口收汇基数内人民币盈亏三项指标切块承包到市县,省公司与地方采取“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联营方式,确定分市县蚕茧、厂丝收购、调拨分配基数和外贸创汇承包基数,与14个重点市县签订联营出口协议。省主管部门为加强货源管理,促进出口创汇,相应制订留成外汇管理、茧丝绸出运证管理及丝类产品征收调节基金等办法,以确保外贸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这一期间,浙江丝绸行业管理,科研、生产、贸易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行业组织“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工作,全省有2家丝绸企业获得国家一级企业,18家获国家二级企业,48家获省级先进企业。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成为全国丝绸业首家经贸系统国家二级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10年间,浙江丝绸行业技术改造完成投资3.71亿元,用汇4264万美元,实施技改项目218个,引进项目30个。引进自动缫丝机,改造水处理设备。省内4个市县13家企业分别引进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家剑杆织机、喷水织机、片梭织机共579台;同时引进先进印染和缝纫设备,改造并建立深加工生产线,提高了浙江丝绸国际竞争力。丝绸科研取得了一些突破,尤其是真丝高档印花绸生产,真丝绸星形架精练工艺及设备研究,涤纶仿真丝后整理工艺及丝绸后处理的计算机应用等项目获得了国家和省级奖励,在丝绸行业产生了良好经济效益。在开拓市场,扩大出口方面,提出了“重点巩固港澳、东南亚市场,全面发展欧美、日本市场,积极开拓苏、东(欧)和其它市场,扩大浙江丝绸高品质、深加工、新品种市场覆盖率”的战略目标初见成效。1990年,省公司统计出口创汇首次突破4亿美元,达4.23亿美元,欧美、远洋市场覆盖率明显增加,制成品等深加工产品出口比重由1985年的7%上升到1990年的21.5%,提高了出口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
1991年,浙江省丝绸行业深入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加快丝绸企业科技进步,抓好丝绸品质综合治理,深化丝绸外贸体制改革。这一年,新开技改项目14个,实际当年完成投资7500万元,不少丝绸企业引进喷水织机、剑杆织机等先进设备。“七五”期间国家科教攻关项目如星形架精练设备、D301A自动缫丝机等成果得到推广应用。针对因“蚕茧大战”造成丝绸产品质量下降的弊端,丝绸行业从改良蚕品种,改进生产工艺,狠抓丝绸品质综合治理。全年白厂丝正品率达到99.95%,平均品位3A+20,丝织品成品一等品率达83.2%,全省79只丝绸产品被评为部优,杭州东风丝绸印染厂的凯地牌115/114真丝印花双绉,杭州春雷丝织厂和杭州红雷丝织厂的保俶塔牌38/37×1真丝和服绸获国家金质奖,湖州丝绸印染厂和湖丰绸厂的真的美牌92.5/91真丝染色双绉、杭州丝绸印染厂、临安丝绸总厂和桐乡石门丝厂的保俶塔牌116/114真丝染色花绉缎、素绉缎获国家银质奖。10月下旬,江泽民主席视察杭州东风丝绸印染厂,鼓励丝绸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增加效益提高竞争力。
是年,丝绸行业实行新一轮外贸承包,由省公司向省政府承包出口创汇、上缴中央外汇和外贸出口运筹基金三项指标,由各市县政府承包上交丝量。省公司把丝绸出口战略重点放在开发新品种,开拓多元市场,改进对外服务,提高出口声誉上。采取以质取胜,以新取胜,扩大推销等措施,使出口创汇达到4.5亿美元,其中省公司创汇3.91亿美元。当年5月25日,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台湾《商业周刊》社和香港洲际美术广告公司联合举办了台湾“幸运佳偶”丝绸之旅活动,提高了浙江丝绸知名度,促进了海峡两岸丝绸贸易和友好往来。
1992年2月,气势辉煌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杭州玉皇山下隆重落成。该馆分序厅、历史文物厅、蚕丝厅、染织厅和现代成就厅,收藏和陈列历代丝绸文物及各省各民族传统生产机具等,成为中国丝绸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一年,浙江省丝绸行业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和中共十四大精神鼓舞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技改步伐,做好产销衔接,保质保量抓好成交出口,使当年丝绸工业总产值增长17.46%,产品产量、工业利税、出口创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同年6月,杭州海关授予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为“海关信得过企业”。
1993年,浙江省丝绸行业深化改革,转换机制,调整结构,开拓市场。尽管蚕茧生产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减收2万多吨,而缫丝生产加工能力扩大造成蚕茧原料缺口达1/3以上,但全省丝绸工业生产仍保持高速增长,全省系统内归口企业丝绸工业总产值增长23.38%,丝绸服装产量2350万件,增速达80.77%,实现利润达3.46亿元。实现了产量、产值、利税同步增长。是年,浙江省丝绸行业突出抓好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增强企业活力。全省丝绸系统加快经营机制转换步伐,先后组建了花神、三环、富泉等企业集团和中外合资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壮大了经营规模。省公司走工贸结合、进出口并举、内外销齐抓之路,形成外贸、实业、进口和内销、海外企业四个轮子一起转,规模经营、整体联动新格局。为稳定出口货源,密切工贸结合,省公司分别与全省出口厂丝的主要生产厂家及和服绸主要厂家联合成立茧丝经营分公司及和服绸经营分公司。在实业投资方面,省公司拥有中外合资企业27家,联营企业27家。同年,省公司正式开始进口贸易业务,第一年进口额达2800万美元。至年底,省公司在香港、日本、波兰、德国、美国、西班牙建立6家海外公司,为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1994年,全省蚕茧产量继续下降,而缫丝加工能力仍盲目扩大,造成蚕茧原料供求严重失衡,蚕茧价格大幅上扬。同时,国际丝绸市场疲软,茧丝绸出口价格下滑,出口竞争加剧,丝绸行业形势十分严峻。省公司为扭转不利局面,抓住出口创汇这一中心,采取措施稳定货源基地,稳定传统市场,实施出口市场、品种多元化,加大对新产品、新市场开发力度,使东南亚、南非、西非、远洋等市场出口能力有所增强。这一年全省国有丝绸工业企业利税总额下降42.6%,亏损企业达到40多家。但仍有一些机制活、管理严、技术高的企业逆势而上,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三塔丝针织集团公司、绍兴丝织厂、绍兴富利达丝绸印染有限公司、新昌丝绸厂和浙江制丝二厂6家企业利润总额占全系统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是年,浙江省丝绸行业继续转换机制,调整结构,以提高抗风险能力。成立以嘉兴丝绸公司为核心的浙江嘉兴丝绸集团公司、以嘉兴绢纺厂为核心的华绢集团,以湖州丝绸印染厂为核心的浙江天昌丝绸集团等8家丝绸企业集团。这些集团联合了300多家丝绸企业以及能源、交通、房地产、金融企业,全方位开拓、多元化经营。特别是11月份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浙江丝绸集团,以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为核心,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33家企业为紧密层,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等43家企业为半紧密层,浙江金三塔丝针织集团公司等173家企业为松散型组成的一个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经济联合体,使浙江丝绸行业在集团化、实业化、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步伐。
“八五”期间(1991至1995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浙江省丝绸行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浙江省丝绸行业面临的困境而言,首先是许多地方的丝绸企业未能及时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盲目扩大生产能力,使丝、绸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原料供应可能和国内外市场销量。其次是国际丝绸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丝绸产品积压严重,国际市场售价下滑,丝绸行业竞争激烈。三是长期积累的供求失衡,机制不活,应变能力较差,加上市场疲软等原因,因而1995年全行业大面积出现亏损。亏损总额为3.43亿元,个别企业已资不抵债。尽管如此,“八五”期间浙江丝绸行业仍得到了良好发展。一、技术改造加快,装备水平提高。共建成投产项目120项,投资额27亿元,用汇2.8亿美元。自动缫丝机比例从“七五”期间的7%提高到16%,无梭织机从2.7%提高到16.9%,印染整理技术改造着眼于配套成龙,丝绸服装企业大多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使深加工能力提高。二、加快了产品结构调整步伐,产品档次明显提高。浙江省丝绸进出口公司于1993年开始推出代表浙江丝绸高档次的凯喜雅(CATHAYA)白厂丝、绸缎、真丝服装等名牌产品。杭州凯地公司的真丝印花绸,绍兴富利达公司的防羽绒面料,嘉兴华绢集团的高档无疵绢丝系列产品,嘉兴金三塔丝针织集团的真丝针织系列等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八五”末共有14只产品成为浙江省名牌,8只产品获国家金质奖,14只产品获国家银质奖,上百只(次)产品获部优产品奖。三、八十年代后期丝绸砂洗工艺的突破和广泛应用使砂洗丝绸服装成为全世界消费热点,国际市场丝绸服装销量大增。浙江省丝绸行业采用中外合资等方式建立丝绸服装中外合资企业,丝绸服装加工和出口迅速增加,丝绸服装生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八五”期末(1995年),全省有专业丝绸服装生产厂家377家,从事丝绸服装生产的企业数千家,年产量达亿件,出口创汇6.5亿美元。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富兴丝绸服装有限公司、杭州华谊服装有限公司等成为生产和出口大户。四、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了丝绸行业整体素质。“八五”期间,浙江省丝绸行业建立企业集团23家(省批)、股份公司6家、有限责任公司20多家,8家企业列入全省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其中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全国丝绸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五、盘活资产存量,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嫁接、合资、引资等办法积极利用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如嘉兴市本级兴办22家中外合资企业,从生产高质量的打线丝到织绸、印染和服装,总投资5298万美元,利用外资1948万美元。杭州市实施“退城进郊,优二兴三”战略,“八五”期间企业数从35家调整到20余家,兼并7家。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实施三一一工程,即建三个生产基地,一个旅游设施,一个专业市场。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存量资产,增强了发展后劲。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拓展国内外市场。全省共有20家自营出口企业,10家海外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出口销售网络,浙江丝绸行业已于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湾地区的1500多家客商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全省丝、绸、真丝服装等出口创汇达10亿美元以上。同时,国内销售建立了大型丝绸市场,如杭州中国丝绸城,(嘉兴)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湖州丝绸城等。
据1995年第三次全省工业普查统计,全省全社会各种所有制形式丝绸工业企业(不包括丝绸服装、丝绸机械工业企业)2650家,工业总产值298亿元。上交税金10.8亿元。在1259家乡及乡以上丝绸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127家,集体企业1002家,股份制企业6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90家,吸引外资5.4亿元。乡及乡以上丝绸企业工业总产值215亿元,上交税金9.0亿元,出口创汇10.5亿美元。有立缫机35412台,自动缫丝机6576台,绢纺锭175267锭,剑杆织机3018台,喷水织机6852台,片梭织机2809台,各类染色、印花机1718台,职工人数38.64万人,总资产255.18亿元。
1996年,是浙江省丝绸行业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丝绸行业环境尚未改观,全行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在体制、管理、市场等方面挖掘潜力,克服困境,省政府于3月份决定对全省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实行贸工农一体化改革。当年有淳安、安吉、诸暨完成了一体化改革,运行情况良好。是年,浙江省丝绸行业成立全省丝绸名牌推进委员会,制订浙江丝绸创名牌目标和措施。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以名、优、新、特产品吸引客户。省公司联合新品种开发科研机构,开发并推出新品种、新花样绸缎116只。各地丝绸企业继续转换机制,盘活资产,压缩库存,拓展市场。但全省蚕茧收购仍大幅减产减收,工业总产值下降6.04%,丝、绸、服装全面减产,全省预算内丝绸企业经营效益有所好转,减亏59.4%。
1997年,浙江省丝绸行业形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由于1996年蚕茧大幅减产,蚕茧供应紧缺,干茧、厂丝价格涨幅较大;二是受市场疲软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丝绸出口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三是丝绸工业企业困难依然很大,资金压力较重。1997年企业流动负债净增3.1亿元,负债率高达73.0%。是年,国家加大了丝绸行业宏观管理力度。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茧丝绸协调小组和中国纺织总会关于调整缫丝、绢纺加工能力的意见。《国家厂丝储备管理暂行办法》、《国家茧丝绸发展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先后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了省公司《关于全省丝绸行业整体结构调整方案》。是年,浙江省丝绸行业继续推进一体化改革。全年已有17个市(县)实行贸工农一体化茧丝绸经营体制改革。省公司会同省计经委、省工商局组织了检查组对全省缫丝企业进行摸底调查,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缫丝企业整顿。通过整顿,发放准产证的缫丝企业178家,生产能力61.86万绪,分别为整顿前的43.5%和56.7%。作为丝绸主产区的杭州、嘉兴、湖州被列为全国优化城市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省公司对试点城市丝绸企业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的有24家。杭州市把“放弃缫丝、压缩绸缎、整顿印染、壮大服装为重点的最终产品,以最终产品带动销售增长”作为结构调整重点。到1997年,东升丝厂进入规范破产,春光丝织厂并入都锦生丝织厂,春雷丝织厂并入西湖丝织工业公司,筹建西湖春雷有限公司。幸福、天成合并筹建天成幸福集团,震旦丝织厂、杭州绸厂并入杭丝联,红峰并入红雷丝织厂,九豫、云裳并入杭州丝织总厂,杭州丝绸练染厂与喜得宝合并筹建喜得宝集团。同时,实施“退城进郊”战略,都锦生、福华丝绸厂、凯地丝绸公司生产车间迁离市中心,并在原厂址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1997年,全省蚕茧生产9万吨,收购6.9万吨。系统内丝绸企业统计丝绸工业总产值63.6亿元,丝类产量11367吨,其中白厂丝9657吨,丝织品产量30269万米,其中真丝绸5619万米,练、印、染丝织品16720万米,服装1822万件。全省80家预算内国有及国有控股丝绸企业亏损1.42亿元,减亏8600万元。全省丝绸出口创汇总额仍达10亿美元以上,其中省公司出口创汇35268万美元。到年底,浙江省丝绸系统归口管理企业共286家,其中系统内149家。而全省全社会各种所有制缫丝、丝织、印练染丝绸企业合计为2600家以上。
(五)
新中国成立后48年间,浙江丝绸行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丝绸科技全面进步,花色品种更新换代,丝绸工业形成规模,国际竞争后劲增强。
“九五”期初,浙江丝绸集团公司制订了《浙江丝绸“九五”计划和2010年目标设想》。明确了“九五”发展和2010年目标设想的指导思想,发展方针,发展重点,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对策措施。重点确定了浙江省丝绸行业丝绸产品向技术含量高,加工精致、质量高档方向发展,培育世界名牌,促进浙江丝绸业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并且实行贸工农一体化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发展企业集团,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加强高新技术改造和研究应用,采用新思维、新办法,加快拓展国际市场等措施,力争使全省蚕茧产量到2000年达到15万吨,丝、绸、服装产量增幅达到30%以上,出口创汇2000年达到12.6亿美元,2010年达到25亿美元。
世界迎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浙江省丝绸行业必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崭新姿态满怀信心进入21世纪。浙江“丝绸之府”地位定会更加巩固,前景更加美好!
(来源: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27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270号 